访谈人:杜荷语
受访嘉宾:吴清顺
杜:清顺你好。时光走笔,草木一秋。我们一起扛过了艰难的七月和八月,来到了崭新的九月。欢迎你,来到全新的“文青访谈”栏目。在这段时间,你是否创作了与抗洪或者抗疫题材相关的作品?你认为这两场刻骨铭心的灾难和这一个多月的封闭生活,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吴:在那段时间,我为7·20郑州特大暴雨洪灾写了两首短诗,有几句是这样的:“我们目睹人世间轰然坍塌的事物,并为之悲悯”“在以后的日子要记得我们此时失落的哭泣/为城市、为亡者的祷告与叹息”。
因为暴雨和疫情的影响,在这一个多月的封闭生活中,我去阅读,读同代人,读先贤与哲人,读诗歌、哲学,在他们的文字中我看到无数的人们在追问相同的命题。我们一遍遍涉足相同的命运,不断勘探生活、命运与世界的界限,对生活和生命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我开始审视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卑劣与懦弱。我审视城市与故乡的关系,我审视生存的意义,我反思灾难带给人们的启示和教训。诗歌让我懂得,生命的现场,需要记录与抒写。经过了洪灾和疫情,今后的诗歌写作可能会更加的关注时代和当下的命题,关注同代人在广阔的世界里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特征。
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学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那么,你开始创作多久了?是什么影响你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呢?
吴:我是从高中开始写一些不成文的文字,当然那个时候远远不能称之为文学创作,只是一种生活记录,现在来看当时的文字不免幼稚甚至过于情绪化。但那些文字在呼吸间,在睡梦中,在鲜活平淡或是枯燥乏味的清晨和午后里,在一日又一夜的光阴流转里,一个个字,一句句话,记录着那支零破碎的情感,那已日渐消瘦的记忆,那正日益远去的背影,那当下发生的未来还将继续进行的故事与感情,陪伴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捱的时刻。
是什么影响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我也说不太清楚,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也并没有对我有过什么特别的要求或者期望。小时候由于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方式,我就对一切记录着文字的纸张、报纸、旧书籍投之以极大的热情和渴望,从旧书摊中疯狂地野蛮生长,那时是真的有一种对文字世界的赤诚的求知欲望让我片刻不停地去阅读。初高中时也有一些内向,基于一种表达和诉说的欲望,之后的写作就好像是顺其自然了,通过文字抵达最深处的悲欢,并流于笔端,成为一瞬间永恒的存在。
杜:清顺,我了解到你目前创作的主要体裁是诗歌,但在你创作初期并不是这样。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变化?你是怎么理解自己创作方向的转变的?
吴:最开始我写得是随笔散文,松松散散地记录和抒写生活。创作方向的改变是源于一场夜谈,2020年在信阳的一次文学笔会上结识了付炜兄长,当时付炜是和信阳作协的前辈老师一起过来的,我们刚好安排在了在一张桌上。酒过三巡,晚饭过罢,付炜约了说要聊聊天,我们在宾馆的房间肆意地聊着童年、文学和创作,聊着青春、诗歌和经验,顺着信阳的老城区街道,我第一次见到申城的夜晚。那次夜谈对我来说不亚于一场海啸和颠覆,我第一次见到了同代人的诗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文本的外延意义、词语的异质组合、语言的独创性、写作的完成度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反思自己的文本。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读去接触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文本加以克制和深入,至今依旧在探索诗歌的道路上。
创作方向的转变我觉得是很普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由散文转向诗歌写作,我认为是一种尝试和突围,是一种永不甘于静止地创造,是在不停地寻找写作的本质和意义。现在进行诗歌写作并不代表以后就束缚于这一种形式了,我觉得青年一代应该要有更多的尝试与可能。
杜:作为一名工科生,你认为如何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寻找诗歌创作的可能性?你对于“理科生爱好文学”怎么看?
吴:日常生活是生命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对日常生活借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记录和抒写,是一种生命个体存在的证据。囿于人生和经验的困顿,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寻找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诗歌写作者必须同时代和生活很贴近又有一定的界限,保持一种疏离,以进入的身份、共情的悲悯、冷静的视角来体察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微小的事情,这种独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与世界认知是进行诗歌写作的必要条件。
“理科生爱好文学”我觉得一种标签化的认知。其实文学是朝着每个人平等地开放,在文学殿堂面前,无关性别、无关身份、无关地位,每个人都是谦卑和渺小的存在。不必局限于身份,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是可以坐在一起交流和探讨的。
杜:在日常学习生活和进行文学创作之外,你还参与了大量文学工作。那么清顺,你又是怎么平衡学习、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的呢?
吴:对于一件事情投入太多精力势必会影响生活或者学习的,这中间的度需要自行把握,明白自己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不沉溺、不迷失,有所取舍。
我在学校内担任扶觞文学社社长,组织一些内部的交流活动,利用周末或者闲暇时间也会参加一些郑州的诗歌沙龙活动,我觉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内心是愉悦的是充实的;之前还在郑州朔北文化艺术馆任职,由于精力有限,在任职一年多后选择把工作交接完申请离职了,但现在回想在朔北任职的期间依旧很感动,有许多难忘的瞬间,大家一起为着青年文学发声做事,是一段极难忘却的经历。
杜: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的创作题材有很多是取材于生活的。有哪些素材被你用进了诗歌呢?它们对你来说有何特殊意义?可以结合具体作品来谈一谈。
吴:我写故乡、村庄和父母,他们滋养我长大;我写朋友,他们给予我力量;我追问生存的意义、命运的悲恸,我写生活中的琐碎悲欢、人情冷暖,我写这些,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我的一生。我现在写,以后依旧写。
我在《六月之声》中写:“六月我咳嗽阵阵,凝噎不止。是我/在重温,你苦难而光明的一生”;在《八月》中写:“有时我想向你坦承,这一生/有太多泪水/没有为你而流”;在《九月》中写:“这一生,悔恨的事物已落满人间”。
诗歌写作诞生于真诚之中。在绝望的腹部,我为诗歌留下我的饱满与真诚。我坦裸一切,在诗歌中找寻遗失的岁月,时刻都在以虔诚等待幸福地垂顾。
杜:在读了你许多作品之后,发现你常常使用诸如“暮色”、“落日”等意象,诗歌的基调也往往比较“悲”。你认为自己的创作风格是较为固定的吗?为何会偏爱这样的创作风格?
吴:除了你说的这种沉郁风格外,我也写过一些比较清新明快的诗歌。一段时期的创作风格是特定时期生存状态的一种映射、一种对生活的质疑和审视。写出这种风格的作品,是跟我的生活背景与经历有关的。我并不会过多的或是刻意的追求某种创作风格,诗歌的写作是个人的行为,诗歌的反映却是时代的映像,用恰当的方式来完成诗歌写作,我想这就够了。
杜:在创作历程中,有哪位作家或诗人带给了你最大的影响?为什么?
吴:我深知自己的浅薄、匮乏与无知,试图靠阅读找寻生存的意义。我的阅读是驳杂的,我读余秋雨、李诞、海子、里尔克、阿多尼斯、鲁米、博尔赫斯、阿赫玛托娃、佩索阿、许立志、黄灯、艾略特、紫金陈、克里斯蒂、王小波、费孝通、黑格尔、加缪等人的作品,我也读网络文学、通俗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些作品,我在这其中汲取到了很多的养分,这种阅读的积淀是我写作的根基。囿于阅读尚浅思考尚浅,硬要说哪位作家或诗人对我的影响很大,倒不如说周围的写作的朋友和老师对我影响更大一些,我们时常交流探讨诗歌和文学,阅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与师友这种交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杜:你认为,文学或者诗歌于你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你的文学追求或者文学理想是什么呢?
吴:某种意义上,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救赎。我在微信读书个人主页的介绍就是:“不读书,不能言。文学,治愈我的人生。”我在阅读中思考,长久地凝视着自己黑暗的一部分,并试图找到光亮,而这光亮就是写作。在文学世界里,我能够看到人们千百年来共有的疑问和困惑、痛苦和悲哀、欢乐和幸福。在贫瘠的原生土壤中,依靠文学,我拥有了破土重生的勇气和希望。
还记得当时看完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我的内心是十分震颤的,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发展成果并没有公平的分配到每一个人身上,甚至有些人正逐渐落后、掉队,成为“物化”的存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与受到的不公待遇,他们很难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去跳出底层的沉默,去表达诉求,去寻求帮助与关注,去寻求解决与善待。他们习惯于被表达,被抒写,同代人往往关注于时代的繁荣昌盛,而把时代阴影下的尘埃忽略掉。这种真实的底层生存图景促使我关注更广阔更真实的时代,让我的写作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
文学创作要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我认为写作者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不只是再仅局限于一人的伤春悲秋遣怀抒情,更重要的是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将视角转向那些陈旧的、破碎的、尚需得到关注的地方,用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进行真实的书写。
杜:现在有很多大学生都在尝试进行诗歌写作,有时候会陷入迷茫和误区。你对他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吴:勤练笔,保持阅读、自省和敏锐度,多走出去与写诗的朋友交流。
作者介绍:

吴清顺,2001年生,河南南阳人,就读于中原工学院。现系河南省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青作协会员、渌水诗社社员,作品见于《奔流》《鸭绿江》《雨露风》《散文诗世界》《中学生百科》等刊物。运营有微信公众号:文艺复兴H。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墨风文化 » 文青访谈第三十四期||一场不甘于静止的突围(吴清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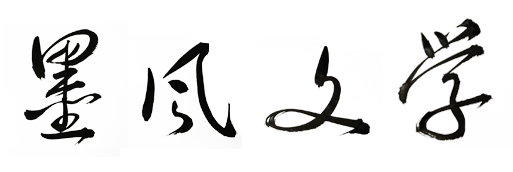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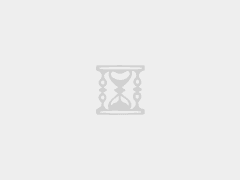
 文青访谈第三十五期||谛听灵魂深处的声音(杜荷语)
文青访谈第三十五期||谛听灵魂深处的声音(杜荷语) 文青访谈第三十三期||陈宇轩
文青访谈第三十三期||陈宇轩 文青访谈第三十二期||卢世龙
文青访谈第三十二期||卢世龙 文青访谈第三十一期||浮生清苦,有你即甜(程浩师)
文青访谈第三十一期||浮生清苦,有你即甜(程浩师)